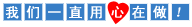人类文明虽然建立在和平协作之上,但也为政治暴力带来诱惑。苏美尔诸城邦的出现标志着农业出现剩余品,于是带来了集权统治。随后不久,人们又将精力花在战争,花在制作金属头盔、矛和盾上,以准备城邦间互相厮杀和与外部野蛮入侵部落作战。到了公元前3000年,城邦间的战争已屡见不鲜,各城邦效仿闪米特游牧部落,建起了半宗教性质的“王国”,不断侵犯那些自己建立起来的,生活基本安定平静的教区。权力集中于个人手中确实有助于改进局部防御,抵抗外来的凶猛进犯,有助于构筑巨大的城墙,但城邦间的混战愈演愈烈,致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消耗于这方面。“强权能吞并弱小权力中心,同样也能刺激敌对权力中心增强自身”(迈克尼尔,1963),闪米特游牧部落阿卡德人以其军事化的游牧生活方式同化了苏美尔人的技术,这就意味着到了公元前2000年后,随着用军队来组织水利工程建设,水利灌溉技术也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公元前1700年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国王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将散居在王国内各保有地上的成千上万军人的姓名、地址和任务等登记造册,从而解决了既要维持一支来自广阔农业基础的人数庞大的职业军队,又能对这支军队实施中央集权控制的困难。
相比之下,埃及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首先产物则由于大沙漠的阻隔而幸免于野蛮的入侵。尼罗河是埃及的一条大动脉,河水缓缓北去,因有盛行风而便于船只逆流航行。通过控制航运业,统治者就可有效地掌握整个农业耕作的剩余部分。这里不必进行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尼罗河成为建立早期和持久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纽带。在埃及,贸易是由王室操纵的,而且它还是一种军事职能,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远征,从叙利亚运回木材,从西奈搞回铜,从努比亚弄到金,而从乡村则征收到税金。可见,从人类文明开始以来,在政治、军事和贸易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上述城邦文明文化和欧亚西部草原亦武亦牧部落的技术和思想相结合,大大促进了社会和政治的进一步复杂化。这一结合在军事方面的表现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发明了轻便双轮马拉战车,不久这战车就成为席卷欧亚的胜利之车。公元前3000年左右,草原牧民开始驯化马匹。将马匹套在轮式车辆上,是苏美尔后裔美索不达米亚人最先搞起来的,但是他们的四轮马车拐弯要靠拖转,因此,不适于作战。后来,一种双轮马车设计出来了,这种车采用轻便的辐轮,而且配有能将车体部分重量传递给马匹的挽具,从而满足了速度快、转弯灵活的作战要求。双轮马拉战车是这一时期的新型装备的主要组成部分。随后,出现了威力极大的复式弓弩,与此同时,在开阔地上构筑矩形土木筑城这种作法也盛行起来。这样,机动火力和快速追击,往往使得那些头戴铜盔、身着铜甲、队形密集的步兵溃不成军。为防止敌方突然袭击马拉战车军营,在其四周筑起方形土城,从而为城市设防提供了基本模式。
随着新战法的采用,草原地带的牧马人将这种新战法与其好战的气质和强有力的部落统率机构结合起来,从而变得不可一世,他们的扩张改变了欧亚大陆的社会面貌。两河流域的文明无力阻挡先进的战车技术。连绵不断的征掠极大地改变了权力的分布,造成了人们的迁徙和同化。马拉战车战术的一统天下在西欧和北欧的山林地带受创。这是因为箭术和战车只能在开阔地上发挥特长,而能使之发挥特长的开阔地位于东方。因此,到了公元前1300年,新技术、新战法迅速而间接地扩散到黄河流域,并在公元前1500年到1200年间由雅利安人传入印度北部。长期的征讨和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战争形式导致剩余产品集中,而这不仅维持了地方暴力、剥削和残忍,而且也哺育了文明艺工和一个有闲阶级。这种基于陆地的黩武主义使早先沿欧亚南部的海上联络慢慢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各文化发达程度不等的民族之间发生不断的侵略性的竞争,从而推动了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极大的推进了一系列同期性文化的发展,以适应增强建设和扩展势力的需要。
本文标题:军事技术与强国的地理
手机页面:http://m.dljs.net/dlsk/zhanzheng/10006.html
本文地址:http://www.dljs.net/dlsk/zhanzheng/100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