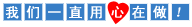从民族语言、古称、自称及地理分布考察,布依族与壮族具有同源的关系。我国古代越人,人口众多,分布范围很广。分布于两广、贵州一带的西瓯、骆越等族是古代越人的组成部分。现代壮语、布依语与史书记载的骆越语(或称萎语)相同或近似。这是壮族、布依族同骆越人渊源关系的有力证据。此外,古代越人的风俗习惯,如居住“干栏”、敲击铜鼓等等,现代壮族、布依族中仍有遗存。
有学者认为,西汉时的“夜郎”国与布依族有一定渊源关系。其证据为:“夜郎”国辖地虽广,但其中心区当在布依族聚居的今贵阳市、安顺市、黔西南或黔南自治州一带;其次,“夜”与“越”、“郎”与“骆”音近,而“郎夜”(即“夜郎”)与“骆越”含义也是一样的,意为“以郎氏为首领的越人国”。“郎”、“骆”是古代越人对“郎”氏族王、官、领袖或头人首领的音译。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相传“夜郎”出自“竹子”(即竹笋),长大后有德于西南夷,是为夜郎王。子孙相沿,以“郎”为首领或当官的。今布依、壮语仍称竹笋为“ranz”,译成汉字就是“郎”。明清称“土官”为“郎”,“汉官”称“汉郎”,又侮称变成“狼”。后来汉族却逐步用来称呼其族或其地。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布依族、壮族被称为“俚僚”、“蛮僚”或“夷僚”。五代以后称布依族为“仲家”,宋代称壮族为“壮”。“仲”与“壮”同音异写。后来,由于长期分居,便逐步形成了布依与壮两个民族。
考古工作者在贵州省安顺、贵阳及黔南等现布依族聚居区出土了数十件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其中一些石器,如有肩石锛、带肩石斧等,其形状与东南沿海及华南地区的同类器物形状很相似,可能这些都是古代越人遗留下来的文化,同布依族先民有密切联系。
秦、汉时代的布依族地区,已经产生世袭的王或侯。王侯居住的地方已经形成了“邑聚”,并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这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已有较大发展。据考古证明,在布依族地区出土的两汉时代文物,主要是铜器和铁器。例如在黔西南州发现汉代的青铜犁、锄、斧、钺,清镇十八号墓出土汉代的青铜剑和钺,以及其它地区出土的汉代铁制锄、锸、铲等,表明当时布依族地区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但比中原地区落后,仍停留在铜铁并用阶段。这种情况,同《华阳国志》所说“畲山为田,无蚕桑,颇尚学书,……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是一致的。
西汉以后,“夜郎”地方政权被汉王朝所统一,置牂牁郡。从此,布依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接触逐渐增多。唐代,中原王朝在布依族地区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县,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刺史,世袭其地。五代时,增设了“八蕃”土司。宋朝继续推行“羁縻政策”,分别授给当地首领以刺史、司阶、司戈、将军等职衔,分别划归四川路、湖南路和广南西路节制。元代置罗甸宣慰司(安顺市属其地)、顺元路军民安抚司(贵阳地区)、都匀军民府(黔南州部分县属其地)、于矢部万户所(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市盘县属其地)及泗城州军民府(黔南州部分县属其地)等。明代的土司制度更加趋于完备,一直到清雍正年间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以后,统治布依族地区达一千多年的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才逐步结束。
明末清初,布依族地区社会生产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期,农具中锄头的重量和长度都普遍增加了,锄口也由过去的贴钢改进为夹钢;稻谷脱粒由从前使用棍棒改为使用挞斗,劳动效率大大提高。罗甸、安龙和平塘等地还使用了水碾。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粮庄百姓”和“私庄百姓”逐渐发生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人日益贫穷而沦为佃农,另一部分却日益富裕而形成富农、地主。而清朝“改土归流”运动,为布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客观上加速了布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领主经济、土司制度的崩溃。但是,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却越来越加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起了布依族人民无数次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发生于清嘉庆二年,由安龙县布依族农民韦朝元(号七绺须)、王阿崇(号王囊仙)和汉族桑鸿升领导的“南笼”起义。王阿崇是清朝中期布依族一位杰出的农民女领袖,出身于贵州安龙县洞洒寨的贫苦农民家里。清嘉庆元年(1796年),她与韦朝元一起领导“南笼”农民起义时还不到二十岁。嘉庆三年(1798年)九月,王阿崇等起义领袖不幸被俘英勇就义于北京。事后,当地人民曾把王阿崇、韦朝元等人的塑像安放在安龙县城和当丈寨里,其英雄事迹至今仍为布依族人民所传颂。
本文标题:布依族详细资料(2)
手机页面:http://m.dljs.net/dljx/beike/44238.html
本文地址:http://www.dljs.net/dljx/beike/442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