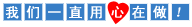理论地理学源远流长。自人类出现之后,他们最早熟悉的知识之一,就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寻求温饱离不开地理环境,辨识方向离不开地理知识,感同身受也离不开地理空间。民族的繁衍、兴衰以及文明的进化,在相当的程度上,都要考虑到地理区域的影响。总之,地理学的产生、演进和发展,无不与人类活动以及人类活动的舞台息息相关。
但是,人类最先获得的知识,不一定就意味着是发展最快和具有导引性质的科学。地理学的沿革及其所表现出的状况,恰恰符合于这一论断。这样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即:地理学的客观性问题和统一性问题。
地球表面既是如此地狭窄,又是如此地广阔,对于原始人或古代人来说,简直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无限的空间。加之地表空间又是如此地复杂;它的基本变化与人的一生相比较,又是如此地缓慢;人类集团所固有的传统和观念,又是如此地顽强。凡此种种,不可能不使得人们对于地理学的认识,产生各种各样的歧见与对立。地理学与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的天然联系,使得它与其他自然学科相比,具有较大程度的主观性。地理环境的千差万别,以及人类的知识水平远未达到认识上的自由,也会使得地理学本身缺乏一种统一的基础。有鉴于此,地理学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就成为在哲学意义上长期关注的焦点。与此相应,我们也就找到了理论地理学的体系长期不能形成和完备的客观原因。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在以往漫长的岁月中,不少卓越的地理学家,均在各自的领域内,为理论地理学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彪炳于地理学史,一直为后人所崇仰。但是,人们仍是不无遗憾地感到:具备统一基础的、可以在总体上加以归纳的体系仍未形成。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随着该门学科的发展,随着学术探讨的深入,其本质越来越被抽象出来,其适用范围也越来越普遍,逐步朝着一种统一的、涵盖更多内容的目标前进。例如物理学中力的统一问题,化学中的元素周期问题,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等,均在某种相当广阔的基础上,概括了那门学科中的普遍问题或本质问题,随着长期的争辩和检验,这些理论仍在不断地扩展和更新。
与之相对照的地理学,似乎先天就缺乏某种统一理论的指导。因此,即使是一些十分成功的结论,也还有待于纳入一种更为普遍的统一基础之中,除非根本否认这种统一基础的存在。洪堡在其巨著《宇宙》第一卷中,开宗明义地坚信这种统一性的存在:“我的主要动机是想把外部环境的现象,都纳入到世界的总的联系之中。自然界是一个被运动着的和被作用着的整体”。我们当然不惧怕这种统一基础出现的缓慢,只惧怕人们根本不屑一顾统一基础存在的事实;我们也不惧怕这种统一基础的不完美,只惧怕地理学家们各执一词而不去寻求共同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明知通向理论之路是荆棘丛生的,却仍要奉献本书的初衷。
长时期以来,在地理学领域内,似乎有太多的时间被消耗在讨论、解释、争辩它的性质、对象、任务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从根本上看,这种讨论不能说是不必要的,它既反映了地理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同时也反映了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地理学在概念上和内容上的不断更新,成了面对新事实、新发现、新水平所作的直接响应。但是毋庸讳言,此类问题的讨论往往有可能导致某种流弊,使得人们陷入到无休止的名词之争或概念的反复澄清之中,至于对地理学的本质认识以及从哲学高度上去规定它的图式和体系,则反而淡漠了。体察到这种状况,国际地理界正在强烈呼吁:完备地理学的理论体系,总结以往地理学家的富有成效的结果,并对未来地理学的发展作出恰当的估计和预测。从这种意义上去理解,本书尝试理论地理学的撰写,无疑是向这个趋势伸出的一只触角。
从1978年开始,一些地理学家倡导“理论地理学国际讨论会”,至今已历4届,无论从参加的人数上,从讨论的专题上,还是从受到的关注程度上和所产生的影响上,都说明了地理学在其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诸方面,正在蕴酿着一个突破性的萌动。这种萌动,既来自于社会潮流的挑战,也来自于地理学家自身的反省,当然也要溯及50年代和60年代计量革命的前期准备。人们很难想象,处于信息时代的地理学,会一直因袭旧的哲学概念而不去变革它;也很难想象在新潮流冲激的时刻,地理学会不去重新思考它的位置和价值。以上种种,汇成了笔者编纂《理论地理学》的动力。
本文标题:理论地理学绪言
手机页面:http://m.dljs.net/dlsk/lilun/7493.html
本文地址:http://www.dljs.net/dlsk/lilun/74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