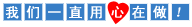六百六十座中国城市中,上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前沿,最能感受着其间所有冷暖,分析它的今天,实是提示中国城市的明天;玉门,地处偏远,因资源兴,也因资源衰,它的背后是中国为数甚多的资源性城市的共同困局,如何寻找并培育城市内生动力,几乎是共同命题;而名不见经传的常德,则是中国规模最为庞大的内陆中等城市的缩影,它的急切,它的惶惑,它偶尔的不知所措,演绎着第三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普遍处境。
在地图上,连线三地,恰是一巨大的折线,这隐喻着新中国城市化六十年苍黄岁月的真实轨迹,而以行政纲领性文件,或一时的主流陈述为线的梳理,实为讨巧而又直指核心的尝试。
城市化有历史,城市也有历史。对于城市传统的延续,对个性化历史的尊重,成为当下城市化进程的显性焦虑,也是考验中国城市化成败的一个关键指标。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方为悟。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做梳理检点,城悟专题,亦期如此。
盛会之后,休养生息?
陆杰觉得自己可以提前退休了,这个坚持用影像记录上海城市三十年变迁的摄影师突然发现自己以后将没什么可拍了,“这至少比我预期提前了十年。”
这一切,都是因为世博会,上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盛宴,陆杰的镜头一度应接不暇。
上海世博会第一次历史性地将园区选址于市区,一个直接目的就是想借机改造南浦大桥两侧这块庞大的工业基地,这实际上也是新上海最后的一块旧疤。现在看来,这一目的顺利达成,尽管黄浦江边的大量厂房被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保护了下来,但困扰城市环境和观瞻的重工业企业已被整体迁移,黄浦江一线流光溢彩已经指日可待。
过去的几年间,以世博会为名,规模骇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工程建设正日渐尾声,这座城市在几乎每一个角落加速度地推进着洗心革面的历程,叉车、吊车、推土机、压路机的身影随处可见。
这样的日新月异一度让陆杰高度亢奋,但他开始担心,这样的惊喜会随着世博会的结束而不复存在。“上海把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内的基础设施投资,一下子都用完了。”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在接受采访时说。
来自上海市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称,2005年至2012年间,仅上海计划新建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就达到10条,新建线路总长389公里,总运营里程达到510公里,短短几年间,上海的城市轨道交通长度就一举迈入全球前三甲,而事实上,就是在五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25公里。
“也许再过十年,上海整个城市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这样了。”在陆杰看来,“上海将进入相当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最多就是在细枝末节上做修补的完善工作。”
上海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郑祖安也坦率承认,“国家一下子能批给上海10条地铁指标的特例恐怕将不会再有了。”
借助于举办国际盛会的契机,在较短时期内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更新的做法,正被学界冠以“盛会模式”而四处被效仿,“说到底,就是短期内集中资源投入建设的过程,缩小了一般的城市演进周期。”郑祖安说。从这一点上说,上海不是始作俑者,“盛会模式”早已在包括昆明、西安、济南等二线城市推广并实践了,但上海确是集大成者。
在这位同时是研究上海城市历史的专家看来,上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没有腾挪空间,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已微乎其微,上海几乎到了没地可批的阶段,“最近几天,市里在各区县调节经济型住房的土地都变得捉襟见肘了,地块少得可怜。”
浦东,未完成的使命
上海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本不应该如此突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经历了围绕深圳特区的改革争论以后,邓小平果断拍板,继续改革开放的思路,大力开发浦东。而在“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年代,浦东相比于浦西,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
二十年后上海的发展,仍没有脱离这一基本格局,事实上,摄影师陆杰所谓的上海没有腾挪空间,主要是指浦西。
4月18日,浦东开发迎来20岁的生日,20年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上海宣布,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宣告了浦东新区的诞生。
一年前的4月29日,国务院明确了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重大政策调整随即而来,5月初,国务院同意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并将其划并入浦东新区。
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浦东新区,面积将超过1210平方公里,较之先前扩大了一倍之多,这一调整,最直接的益处是带来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还直接服务于航运中心。
利好消息亦纷至沓来——2009年11月4日,上海迪士尼项目报告获核准落户浦东;11月17日,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即将落户浦东机场附近地区。
“中央在浦东的发展意图一览无余。”上海社科院一位专家分析,“浦西已经饱和,两个中心全是围绕着浦东,浦东将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唯一变量。”
事实上,在国家对于上海两个中心的明确定位出来之前,近二十年浦东的开发和建设,历经辗转,甚至一度饱受过度依赖政策倾斜的诟病。
在郑祖安看来,在与浦西隔江相望的地方造一个新城,当时除了战略的考虑之外,还包括探索浦西发展出路的问题。
上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心”(地理位置类似于现在的内环),而这个中心的压力,随着经济发展、人口、交通等一系列城市问题的出现而与日俱增,而缓解城市中心压力一直是上海需要解决的难题。浦东开发恰恰提供了突围的机会。“但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如果1990年代我们把行政中心搬到浦东,或许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郑祖安说。在中国,行政中心所在地向来是城市中心所在,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俞正声在主政青岛时期,曾大胆地将行政中心搬迁,而成功实现了城市中心的转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十里洋场的繁华,至今仍是许多上海人挥之不去的浦西情结所在。所以,即便经历了20年的发展,上海的中心依旧在浦西。
输出上海
上海有两条母亲河,一个是浦江,而另一个就是苏州河,这座城市的大起大落尽在其侧。
学者朱长超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的苏州河则是“散发着一阵阵臭气,河面不时冒着气泡、翻滚着塑料袋和破鞋子的黑色河流”。那时苏州河被称为轻工业摇篮,两岸曾聚集了包括上海面粉厂、上海啤酒厂、上海造币厂、上海毛纺厂等一批著名的近代工业。
1990年代,上海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几乎所有的工业企业都进行了产业转移,而这直接启动了大规模的城市腾挪术,苏州河得以恢复了往日的清静。
之前的上海有一个形象的标签:几百万马桶、几百万煤炉。伴随着苏州河产业转移的还包括棚户区的拆迁改造,动辄数十万人的居住动迁,开创了城建中的拆迁之最。至今,仍有很多人将上海称为大拆大建的始作俑者。
在1992年至2000年的第一轮旧城改造中,总计有200万居民搬出了棚户区、老房子,他们沿着尚未建设成熟的地铁和公路,一步步离开了市中心,而他们曾经的房屋所在地则被改造成了一栋栋的高档楼盘。
“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城市建设,同时聚集了开放以前那三十年停滞不前的公共建设和居民住房改善的压力。”郑祖安说,“只能采取激进的大拆大建。”拥挤的公交和狭窄的住房,被称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两大死结。
只是,那场产业结构调整的课题却远未结束,在究竟是以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定位中,上海经历了长时期的摇摆,直到2009年,市委书记俞正声给出了定位:只搞服务业不搞制造业肯定要完蛋。
浦江却不复苏州河回复清静的命运。自1991年起,上海以平均两年一座跨江大桥的速度,相继建造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奉浦大桥、徐浦大桥,直到2003年建成通车的卢浦大桥,试图彻底贯通浦东。与大桥对接的则是中心城区大规模的立交、环线建设,至1999年,耗资超过182亿元的上海“申”字形高架路网基本建成,当时的报道称,“城市地面道路交通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大桥、高架、商业中心,这些城市建设中的必备元素,随着在上海的诞生,也逐渐在中国的各个城市落地开花,是为上海输出。但大拆大建的城市拆迁模式也带来了问题,高房价无疑是其中之一。
让郑祖安更为担心的是历史文化保护问题,最近他在呼吁闸北区政府重建天后宫,所有的海港城市都有天后宫,这是马祖文化的标志。1884年建成的上海天后宫,在2006年的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一个海港城市,一个要做世界航运中心的城市,我们居然把这个文化符号给拆掉了。”
“还有中共一大会址,现在的保留建筑根本不能反映一大召开时候石库门里弄的真实生活背景。”郑祖安说。而中共一大会址恰恰就是享誉国内的旧城拆迁改造模式的“新天地”所在地。
“新天地”的总设计师伍奔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设计新天地的时候,甚至没怎么去想历史保护,“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每个人可以享受这里,这本质上完全是一个商业行为。”
而继上海新天地的商业模式成功以后,“新天地”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杭州、重庆、武汉、佛山,而其他山寨版的新天地更是难以计数。
“上海的城市建设发展模式并不能被简单复制,除去它自身还有一堆问题需要解决外,更重要的是上海的城市建设有其特定的条件,比如说产业结构和上海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政策支持,这都是上海特有的。”上海社科院一位专家说。
本文标题:我国三十年城市化得与失(3)
手机页面:http://m.dljs.net/dljx/beike/28960.html
本文地址:http://www.dljs.net/dljx/beike/289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