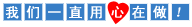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今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和生机勃勃的高科技群体,正在给人类带来震憾。这些凝聚着文明与智慧的先进科学技术,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都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肯定,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于历史责任感,以社会效益为重,出版八卷本《中国当代科技精华》丛书,旨在充分反映我国最新的科研成果,推动我国科学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是一件功不可没的好事。正因为如此,他们约我为这套丛书作序,就颇有些为难了:却之有碍于他们的至诚,于情理所不允;应之而为大师、巨子们作序,又实为不妥。两难之间,只好以倾吐一下我自己步入科学大门的有关经历和感受,权为代序。
能在科学事业中做出成就,勤奋和机遇缺一不可。关于勤奋的重要,从“学而不厌,自强自坚”,“业精于勤,荒于嬉”等千年古训,到现代科学家们的“聪明寓于勤奋”,“勤能补拙”等宏论,都没有异议。对机遇则时有争论。南宋陆放翁风华正茂时主张:机会无时不有,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历尽山河破碎和人生坎坷后,他晚年改变了看法,写下“不如意事常千万,空想先锋宿渭桥”的感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后,出现了“机会主义”一词,泛贬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之徒。从此忌讳讲机遇的人就很多了。然则,历史总在反复证明,国家的兴旺,事业的成功,人生的成就,莫不需要机会。天时地利不常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故近有抓住机遇,不使错过之说。
我能进入科学的大门,甚靠机遇。“九一八”事变岁杪,我出生于山东荣成县,黄海之滨的一个穷乡僻壤。全村世代无鸿儒,户户尽白丁。连年旱灾,人民饥寒交迫。日寇入侵,人民起义,天下大乱。我来到人世后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鬼子来了!”这是大人们吓唬孩子的魔语。我懂得大难临头,不能再哭了,虽然不懂这“鬼子”是何物。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有一位张绍江老师,坚持在这穷村办小学,使我们几十个幼童得以念完小学四年。现在回想,倘如在战乱中张老师走了,我们可能全成为文盲。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攻占华北、山东,胶东各县城镇相继沦陷。日军烧杀抢掳,我们都无书可读了。兵荒马乱之际,谁会想到让孩子们读书?然而,天不忍塞孩子们一隙之明。理琪、林一山等共产党人领导了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第三军,建立了敌后根据地。浴血抗战之时,他们未忘让孩子们受教育,责令各地建立完(全)小(学)和几个战时中学。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又得到机会念完小学五、六年级,于1944年考入文(登)荣(成)威(海)联合中学。日军扫荡,天天逃难,中学无住所,全然是一支“孩子游击队”。学枪、学炮,还似懂非懂地学了“抗日游击战”之类高深课程。1945年德国战败,抗战到了最后阶段。八路军需要知识分子,故解散联中,鼓励从军。我,这个初中一年级尚未念完的“小知识分子”被分配到八路军东海军分区当护士。日本投降前夕,又连精兵简政,一批十三、四岁的“小八路”被精减了,送到刚从日军手中收复的威海市威海第一中学续读。1946年春,风云又变,国共战争有即发之势,同学们又一次纷纷从军。时年5月,我14岁,成为八路军的一名勤务兵。有幸遇到了一位可敬首长,威海市市长兼卫戍区司令员于洲( 1904~1979)。他是山东著名教育家,30年代毕业于北平师范。回山东后办师范学校并任校长。抗战爆发,他成了胶东抗战领导人之一。我酷爱读书,值勤之余,读遍当时威海市图书馆所藏。出于职业爱心,他赞赏我的勤奋,关注我的学习,批改日记,纠正用词,教导我成为一名为人民利益献身的战士。1948年他奉调南下前未忘嘱下属照料和安排我的学习和工作。于洲是我一生中第二位启蒙老师。
1948年秋,我辗转到设在博山市的华东工矿部工业干部学校(今名山东建材学院)学习。我们从数、理、化开始学起,第一堂课便激起我无尽兴致。读似饥餐渴饮,听嫌课节太短,课后余音袅袅,如醉如痴,不能自已。解放战争胜利,共和国成立,要加速结业。同学们纷纷奔赴济南、上海等大城市。而我,在教育长刘辛人、班主任刘孟栋等谋划下,被保送去由苏联教授授课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是他们,在时代的大潮中,将我的命运之舟送上了科技的航程。
1951年春,我只身从山东来到哈工大。经考试,俄语课几乎交白卷。校领导认为学历不够,命我进预科。经过我的抗争,领导人勉强同意我试读。我深知面临严峻的考验,决意不惜代价,昼夜奋战,学习俄语,补习课程。于1952年以优秀成绩读完大学一年级,并顺利通过了留苏考试。
1953年,由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送行,我进入莫斯科包曼高等工学院炮兵系二年级。这是曾造就过苏俄数代科技英才的学府。苏航空巨擘图波列夫、航天之父柯罗略夫(S.Korolev)、数学家车彼谢夫(P.Chebyshev)、力学家茹科夫斯基(N.Rukovski),都是该校毕业生。我遵命学炮兵,但爱好却在数学、力学等基础科学。从四年级起,我昼夜分读于两个大学。在莫斯科大学夜校倾听过世界科学大师庞特里亚金(L.Pontragin)、邓钦(E.Dynkin)等教授的控制论、现代几何、代数等课程,引起我对数学的热爱。美丽的体系结构,严密的逻辑推理,广泛的定理涵盖,真是无边无际,无穷山色。1960年我同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夜校和包曼高等工学院研究生院。
1957年秋,我慕名到苏著名科学家费德包姆(A.Feldaum)教授处做毕业论文,半年后完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三维空间最优控制系统设计和试验。论文发表后,受到各国科学家们的鼓励,这增强了我的信心。进研究院后我仍留在费的试验室,继续做最优控制的研究。一年后基本完成了“最速控制场论”的研究。
天有不测风云,月有阴晴圆缺。我完成副博士学位时,中苏开始论战,两国关系恶化。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对留苏学生采取限制措施,撤回苏联专家。中国上百个发展项目陷于困境。人们无不义愤填膺。我谢绝了数位院士和老师同学要我再留数月,完成博士学位的建议,立即整装回国,投入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三十年河东又河西,80年代末恢复了中苏关系,我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身份应邀访苏,顺回母校,接受了由苏最高学术委员会签发的博士学位证书。他们申明,这是补历史上的阙失。报章发消息后,一位美国教授来信祝贺,说这叫“飞去归来器”——Boomerang。
本文标题:勤奋与机遇代序
手机页面:http://m.dljs.net/dlsk/dixue/20168.html
本文地址:http://www.dljs.net/dlsk/dixue/201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