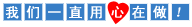这并不是一件神奇的事—
婴孩出生后第一次言语,呼唤的,是妈妈。
我妈妈是我的妈妈,我知道,她不是神仙,因而不神奇,因而平凡。
但我知道,那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岁至中年,不美。土黄的脸上,现出几瓣红,那是冬日留给春的信封,轻轻的染在妈妈的脸上。点点雀斑,如空中落下的灰尘,拂之不去。我心里想着,她是有些老了,眼梢眉
头都皱了。一双眼睛且深且亮,仿佛聚集着无数光似的,如墨玉般闪耀着深沉。爸爸和妈妈吵架时,总说那双是三角眼,但想必也不是一样的吧。
因为这是我的妈妈。
以前,我和妈妈尚未离故土。她每天和我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于是我放学时背回一包书,她背回一包软棉,那棉染了太阳的颜色,又滚烫的似一簇火,像是在妈妈的背上燃烧
。于是我好心的问,妈妈热吗。妈妈总是撒谎说,不热,又眨了眨黑黑的眼,似笑的离谱……可发丝中颗颗汗珠清晰。
我猜妈妈又是在撒谎,是为了不让我有理由去买冰棒吧,于是,我便气呼呼地跑着前面去,与同学一行了。
妈妈,你撒谎说不热,可我是真热呀!你看我这汗淌得……
冰棒呀,你可想煞人了。正幻想着咬那冰棒一口,脑海中无缘故的跳出爸妈年节时,颦眉含嚼着还债的字眼,心下烦了起来。于是抱个书包,扔到桃荫之下,撒欢着摘桃去了……
空闲时,我只憋着不出门,只因还和妈妈赌气,屋子没来由地像火笼一般,热得离谱。我便坐在墙边香樟荫下看鸡掏窝,不过那鸡速度极慢,摆了肉肉的屁股,不停地深入土地,不见成
果,于是我火急火燎地拿来铲子,把鸡拎出浅沙洞,那浅洞圆得柔和,是为鸡屁股量身定制的,于是我动铲,不一会洞有些深了,我又把扑扇翅膀的鸡拎回洞里,于是那鸡便出不得洞了,于
是鸡斜瞥我,像宿敌似的。“这孩子…….”不知何处传来一声浅笑,但为此我仍很是得意。
妈妈饶有兴趣地眯着眼睛看我如何逗鸡玩,,于是我不逗鸡玩了。只故作深沉得看着夏日落叶,那叶都焦如旧纸,又弱又脆,只有香樟树绿的深沉,却压抑忽然想起妈妈的眼,有时亦压
抑却含着离奇地笑注视我。
我硬下心一想,舍不着自己套不着冰棒,于是提着板凳摇着身子走出绿荫,挑了块有光的地方端坐下来,于是我便受着肉体与思想上的重重折磨,但我并不痛苦,不痛苦,真的,我是有
志向的人……
妈妈出去了,临走时我轻瞟了她一眼,她斜着嘴角离奇地笑,黄白的肤色在太阳光下熠熠生辉,汗珠随旧衫滚落,有浸湿了大片,亮而狡黠的双目微微闭着也含着笑,我不知会有什么好
事来到。
妈妈回来,便像看小丑表演似的眯着眼,笑笑地看我,有什么好笑的?我气恼,我这时有些吃饱了撑的,仍托着腮,坐在树荫之外的远方,摇摇地望着田野,仿佛那里能蹦出些什么似的
。
妈妈又盈盈开口了:“四妈等你去吃呢宝贝!”我风似的裸脚奔走,草儿轻轻挠痒,却我这厢皮厚不觉了。四妈一般是不让别人把冰棒存在她冰箱里的,我妈妈却总可以的。我奔去四妈
家熟练地开着冰箱门,拿起角落单独的一支,又拿着旁边最近的一支在四妈眼前女王似的晃了晃便飞似的、长翅膀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