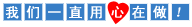他垂着头往家里走,心里像缠了几十道线似的,勒得他难受,复杂得很。今天去讨薪又没成,还差点叫人修理一顿。这钱工头已经拖了俩月了,再这样下去,家里非闹饥荒不可。自己饿着倒不要紧,关键是把女儿饿着了,这小身子板肯定经受不起折磨。 想起女儿,对了,她的学费还是赊着学校的呢,得想法子弄点钱赶紧交上去。想到这里,他的心绪又复杂了几分。
天已经黑了,深长的巷子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扰得人心烦。他看见自家破旧不堪的外墙上,用红色颜料写了个大大的“拆”字。真是一刻都不得安宁。这哪里要拆除房啊,这分明是要把人心给拆喽!
他边愤愤地想着,边扭开家门。看到女儿正伏在一张用几块旧木板拼凑成的写字台上,借着墙角微弱的灯光,一笔一划写着什么。见他回来,女儿轻轻唤他:“爸爸。”他便暂时抛开这些天恼人的烦心事,觉得在外多受点苦也值了。
第二天天一亮他便出门,这工钱还是隔些天再讨吧,眼下还是找些活儿来干为好,这日子紧巴着呢。他走进一建筑工地,问人需不需要帮手,那人眼一横,正眼都不多瞧他,“正好,你去打扛包吧”。说罢,随手一指。扛大包是计件给工钱的,扛一包得两角钱,他起初嫌少了点,但后来觉得总比没有好,于是抓起两大包就往肩上扛。
毒辣的太阳晒得他两眼发昏,渐渐地,他的动作有些吃力,双脚也有些站不稳了。但一想起女儿,就又咬牙坚持了下来。他没命地扛着大包跑,一直干到天黑,总算把女儿那十多元的学费扛下来了。
回家路上,他的脚步有些飘,可不是嘛,终于了却心头一大事了,学费总算有了着落。
正哼着歌呢,邻居王太太拦住了他,请他帮忙去院子里给她家狗喂吃的,自己有事离不开身。他忙不迭地点头,结果了那食槽。别的不说,他这人了大的优点就是乐于助人,别人请他帮忙,只要是他办得到的,从来不会拒绝。另据的人都清楚这点,有事没事总该唤他几声,对他也蛮和气的,餐桌上多的几个包子也会送来他们家。
只是帮的忙多了,大部分又是些三十几岁的女人,免不了招来些莫名其妙的流言蜚语他也不多想,想那做什么,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他块头还算结实,可相貌着实平庸不说,还划上一道月芽疤在左脸上,怪吓人的。口袋里更是没啥钱,穷得叮当响,当初他媳妇就是嫌弃他这点才会结婚没几天就溜了的,还是专心供女儿读书吧。
想到这,他应和别人的声音就愈发的响量,帮人野更加勤快了。
这天他心情特别好,阳光照在他黝黑的脸庞上,有那么一丝血色起来。他是真高兴,用他的话说,那是“比当初娶媳妇还要兴奋”,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张开了孔,舒心得很。那工头叫人抓着了,拖欠了我的俩月的工钱也发下来了,他攥在手里的那个碎花布兜里边,就是刚结下的工钱。有好几张还是鲜艳的红色的呢。他把布兜装进口袋,右手死死地护着,生怕叫人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