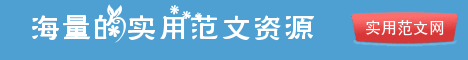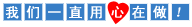算起来,我们这一辈的读者读哲学的时间并不短,但却始终害怕读哲学。因为,哲学书籍常常摆出高不可攀的架势,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弄哲学的人有时也故弄玄虚,把本来可以理解的东西弄得“一些不懂了 ”。西方哲学于文字又隔了一层,我们只好仰仗三家村夫子们的翻译,结果追求到的是影子的影子,离真理更加远了。我自己阅读哲学的经历大抵如此,也许只能怪自己愚钝而没有悟性。有一天,在自己的破书堆里找到威尔·杜兰(WILL DURANT)写的《哲学的故事》,发现原来哲学也并不难读如许。杜兰说读哲学也有快乐,连形而上学都有诱人之处。每个学哲学的人都曾有这样的阅读体验,只是迫于生计,人们在刨食的过程里忘却了这样的体验。诗人勃郎宁说寻找生命的意义是日常必需一如饮食。思索生命意义的过程就是哲学的过程。《哲学的故事》和房龙的《人类的故事》一样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我努力寻找一个学科的边缘而怀有写作热情的人物的著作来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比如,英国的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他的《哲学的慰藉》就给了我这样的阅读乐趣。译者资中筠先生推荐我读这本小册子时,我内心有着一向的对于书的傲慢,并不以为会一字一行一页地读的。及至书到手,不知不觉竟然全读了。资先生的散体文功夫当然给这本书的中文本增色不少。不过,原文据说也得英语古典散文的三昧的。“我一向认为,一种臻于上乘的文字首先是本土的,不是洋腔洋调的……”我把这句话视为资先生的翻译主张。也因为这个我拿到了英文本也不愿意去看。我不想破坏已读中文本给我带来的文字享受。两种文字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好的翻译在文字上应当说是一种创作。莎士比亚之所以在中国脍炙人口,是因为翻译家们把莎士比亚的文字用地道优美的中文转达给中文读者了。我读《哲学的慰藉》一开始就读的是中文本,语感定势有了之后,并没有想到要读原文。这就是有语言魅力的翻译所具有的效果。假如,让我来做文字翻译的裁判,我宁愿给风格记分,而不在科学界定上纠缠不清。因为,任何文学翻译都是不能用科学的手段来裁判的。两个人同为高手来翻译同一部著作,结果一定是两个文本,因为两人的语言感觉和文化理解是各自的。翻译批评如果不考虑这样的因素就谈不上专业。钱钟书说理论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翻译的理论家尤其缺乏实践。鉴于此,我通常不从事翻译评论。这当然也有心虚的原因,一提翻译批评,就感觉人家要批评我自己的翻译嗄。
《哲学的慰藉》书分六章,分别“慰藉”与世不合、缺少钱财、受挫折、有缺陷、伤心和困难的众生。哲学的终极作用大概就在于此吧。真正的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或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哲学家对世俗的东西弃置不顾……你可能以为我会这样引下去。然而我不会。假如《哲学的慰藉》只有这些,我就没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了,这样描述哲学家的书籍太多了,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哲学的慰藉》里的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个别人选如蒙田算不算哲学家,作者并没有按照学院的规定来安排。我接触蒙田超过二十年,《哲学的慰藉》却让我从另一个视角了解了这位随笔作家。饮食男女在蒙田的笔下都有细微的观察,异地风俗也是他散文挥发极致的对象。“我之所以为我,每一样器官都同样重要……我有义务向公众展现自己完整的形象。”在写叔本华的爱情故事时,德波顿说:“我们比鼹鼠总还有一项优势。我们同它们一样需要为生存而奋斗,为繁衍后代而求偶,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去戏院、歌剧院和音乐厅,晚上睡在床上还能看小说、哲学书和史诗……”这种思索本身就很有哲学意味了。写尼采时,德波顿用了“推崇悲苦的哲学家”这样的字眼:“很少有哲学家推崇悲苦。”尼采把大多数哲学家讥笑为“卷心菜头脑”。“说实在的,在活着的人里没有一个人是我在意的。我喜欢的人都在很久以前作古……”关于尼采,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我并不想在这里误导读者。我感兴趣的也许跟哲学沾一点边:资先生做了几十年入世的学问,从事的一直是理性思维。德波顿选的几位哲学家或者思考入世问题的角度不合常规,您翻译时有什么样的感想?人在摆脱了职业读书的羁绊之后,阅读趣味是否更合人性一些?思想的闪光和逻辑的亮点是一回事吗?理性如果能指导实践,思想又能解决什么?与其说这些是我读《哲学的慰藉》时产生的疑惑,毋宁说是读书以来就有的疑惑。哲学如果真能慰藉人生,读书倒是一件幸事。理性思维的极致有时近乎疯狂,几个循环你便找不到北了。这个时候,没有哲学的人可能倒能解脱。如此,幸福倒离无知近一些。